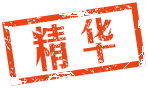请马上登录,朋友们都在花潮里等着你哦:)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x
老家的记忆 一、奶奶 打我记事起,奶奶就是老家的代称,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,六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很穷的,爸爸分的房子,也是十几平米的小屋,我们一家四口人住都嫌挤,更别说让奶奶住我家了。只有特别的时候,不得已的情况下,奶奶才会来我家住,那是弟弟出生的时候和弟弟进托儿所之前,再有就是奶奶有病,需要看病的时候了。而我对奶奶的印象,也只停留在了11岁之前,因为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奶奶就去世了。一些奶奶的记忆,是从妈妈的口里记下来的。 妈妈曾说过,奶奶是个很爱干净的人,平时的时候,穿的衣服没一点褶皱,有一点,奶奶也会把它们抚平,穿身上的衣服奶奶会摸好几遍,上面一根线头都不会有。可见奶奶活着的时候是多么爱干净的一个人呀。 奶奶的身世,我是从爸爸的回忆录里知道的。爷爷上世纪40年代就去世了,奶奶一直一个人过,解放前曾被一个当过汉奸的恶霸霸占过几年,并给他生下过两个女儿,但奶奶并不爱她们,后来刚解放不久,由于村里人和我爸爸的揭发,那个汉奸被政府抓走,好像后来枪毙了。有一年脑炎流行,政府给每个孩子都发了药,而奶奶只让我爸爸一个人吃了,两个女儿没让吃,后来两个女儿都被传染死去了,可见,奶奶始终都恨那个霸占了她的人,和他的女儿。 爸爸的回忆录里还说,他并不是奶奶的亲生儿子,而是爷爷从解放区抱回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,当时还给了两件信物:一只怀表,和一件有洞的毛背心。可惜,爸爸当时脑子有毛病,东西曾经让邻居保管,但这一保管就再也要不回来了,甚至到了我长大以后,报了警,派出所到那一家去,也没要回来这两件东西。因没了证据,而爸爸是不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件事,也就没人再当回事了。 奶奶是个没文化的人,大字不认识几个,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,只有一个小名叫二妞。解放后因为户口登记的需要,奶奶就借用了一个别人的名字叫作了李天恩。要是奶奶活着,能说出很多过去的事,可惜,奶奶没了,什么都带走了。 既然奶奶是个没文化的人,是怎么记住东西的呢,在我的记忆中,奶奶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那里跟念经一样的嘴里不停的念叨着什么,一开始不知道,觉得好玩,后来,大一点的时候,奶奶在念叨的时候,我就会在旁边捣乱,嘴里也叽里咕噜的乱说一起,奶奶这时候就会停下来看着我,脸上应该是有点好笑,有点责备吧。 记忆中,上幼儿园开始,每当放寒暑假,我都会被送回到奶奶家里,当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,后来长大了才知道,那时候大人都要上班,家里还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,放假以后,爸爸妈妈就没时间照顾我了,所以,要被送到奶奶家里。慢慢的跟奶奶就有了说不清的感情,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星期天,爸爸要带着弟弟到奶奶家干活。奶奶家当时还没有自来水,吃的水,要爸爸每周日回去给她挑回家去,要是爸爸有事回不了家,则要让亲戚给挑一缸水。而亲戚间关系并不融洽,所以,奶奶有需要的时候,倒是请外人帮忙跳水的多一些。而奶奶虽说看不见了,但一般的盲人听力都是超好的,单凭听走路的脚步声,奶奶就能听出是不是熟人从门前过,要是熟悉点的熟人挑水从我家门前过,奶奶就会让人家给帮个忙给我们家一担。那次,由于爸爸带的东西比较多,就没让我去,我就一直追着爸爸,哭闹着一定要跟着去,后来爸爸没办法,前面带着弟弟,后面带着我,东西就让我抱着,虽说抱着东西坐车很难受,但跟着爸爸一起回家的渴望让我忽视了坐车的难受感觉。 说起挑水,小时候由于孩子爱玩的天性,有一次我也想去给奶奶挑水,由于不会用扁担,当时人也小,估计当时还挑不动一担水。我就提了一只水桶去打水,由于只看过别人打水,从没有自己打过,桶下到井里怎么也灌不进去水,倒是没弄好,把绳子的挂钩给弄掉了,还是旁边的一个同村大人,眼疾手快,夺过我手中的绳子,及时勾住了桶,并帮我打上来一桶水。由于一桶水我也提不动,只好倒掉小半桶,提着大半桶水回了家,奶奶虽然高兴我能给她干活了,但还是心疼我小,就不让我再打水了。 奶奶虽说看不见,但听觉、嗅觉、反应还是挺快的。生活中我曾经不止一次碰见过不吃熟鸡蛋蛋黄的人,我小时候有几年也是这样,由于奶奶心疼我,每年回家,每周奶奶都会有几天给我煮鸡蛋吃,那时候由于没钱买肉,一般家庭的鸡蛋大都也收起来,等存到一定的量,就会拿到供销社去换柴米油盐针头线脑什么的,当时叫鸡屁股眼里的银行。可奶奶却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,煮了让我吃,由于当时也没条件做茶叶蛋,都是清水煮的,吃过几次就不想吃了,不想吃也不敢扔了,给奶奶吃,奶奶总是找各种借口不吃,我就悄悄的把蛋清吃了,把蛋黄放到门墩上,不知道怎么,不出一天奶奶就会知道了,也不知道是别人经过看到告诉奶奶的,还是奶奶自己摸到发现的。总之,只要我把蛋黄放下不吃,奶奶总会知道,真是神奇的奶奶。 小时候由于物质生活匮乏,别的什么都没有,唯独对吃有很强的记忆。当时的豆腐,都是实打实的豆腐,吃着真好吃,比现在街上卖的三块钱一斤的豆腐还好吃。当我听到卖豆腐的沿街叫卖声的时候,就会停下手中别的东西,很神往的听着叫卖声从村东响到村西,又从村北响到村南,奶奶不知怎么看出了我想吃,就拿了碗,从缸里挖出一碗面给我,让我去换豆腐。一个假期能吃上一次这样的豆腐,那就会记住好几年那个味道。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,奶奶的粮食也是定量供应的,换了豆腐吃,口粮就会少了,会不会到时候主粮不够吃。好在,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,一年能碰上一两次就不错了。 杂面条,是我记忆中的另一种好吃的东西,这个杂面条并不是我们平时吃的杂面,而是没有一点白面的,好像是红薯面和高粱面参合在一起,蒸出来的窝头,然后用机器手工绞压出来的面条,粗粗的,软软的,颜色是紫色发黑的那种颜色,虽说颜色不好看,但用油炒了很香很香的,看着别人家做,我就会馋的直流口水。也许是奶奶给爸爸说了,爸爸来了以后,就会用黑面蒸了窝窝头,切成薄片用油炒了让我吃,虽说没有人家用机器压出来的面条炒出来的味道好,但也算是吃上了一种替代品吧,心理小小的得到了安慰吧。 |